内容提要:李之亮教授是斐声海内外的宋文化研究专家,已有五十余部著作出版。笔者在研究宣传杨家将文化过程中,涉及到宋代历史文化,拜读了他的不少作品,实在获益非浅。但是对他收入《教科书里没有的宋史》中的《〈水浒传〉比〈杨家将〉更真实》一文中的一些观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不揣冒昧,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拓义
李之亮教授是斐声海内外的宋文化研究专家,已有五十余部著作出版。笔者在研究宣传杨家将文化过程中,涉及到宋代历史文化,拜读了他的不少作品,实在获益非浅。但是对他收入《教科书里没有的宋史》中的《〈水浒传〉比〈杨家将〉更真实》一文中的一些观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不揣冒昧,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一、关于《水浒传》与《杨家将》运用史实的问题
李教授首先评价:“同是写宋朝故事的小说,《杨家将演义》和《水浒传》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杨家将演义》属于‘戏说’之列,是穿着宋朝人的衣服说明朝的事,而《水浒传》则属于‘正说’,讲的实实在在就是宋朝的故事,只是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处理”。
就创作艺术性而言《杨家将演义》和《水浒传》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水浒传》是明代产生的文学名著,艺术水平达到了当时长篇小说的空前高度,而《杨家将演义》同样是英雄传奇,只是当时一般的流行小说,比较粗糙,艺术性差。
但李教授说《杨家将演义》属于“戏说”之列,而《水浒传》属于“正说”,这就使人难以接受了。两部小说尽管都是个人创作,但却都是在民间传说的故事、戏剧和话本等基础上加工形成。明代的杨家将题材小说有《杨家府演义》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还有一部是《杨家将》,最早叫《北宋志传》或《宋传续集》,后来人们将两种小说混淆,或称《杨家将传》或称《杨家将》或称《杨家将演义》,主要指的是《杨家将》,说《杨家将演义》是人们对明代以杨家将为题材小说的统称,这并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
李教授说的《水浒传》比《杨家将》更真实,主要是指《水浒传》的史实成分比《杨家将》多。
他说“宋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宋江曾参加征方腊的战斗,而且说“宋代史集中关于宋江的记载还是蛮多的,时间地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大致脉络则没有太大的出入”,他还举《东都事略·张叔夜传》和《宋会要辑·兵》李埴《十朝纲要》中有关于招抚围剿宋江的记载。谈到《水浒传》中的一个“大人物”“梁中书”梁子美也是实有其人,在《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有记载,还提到一些人和事,高俅的发迹,徽宗的荒谬,蔡京的书法,京城名妓李思思,小种相公,老种相公等。谈到《杨家将演义》时说,小说里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在史书里找到一些影子,但仔细一核对,除了杨业和杨延昭外,很少能见到与史实相吻合之处。李教授说,描写最糟糕的当属潘仁美这位为大宋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被严重扭曲,更可笑的是杨门女将云云……。关于潘美和杨门女将的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
从以上李教授列举的两书史实看,水浒传多,杨家将少。其实稍知宋史的人都知道,关于两书的史实根据,杨家将要比水浒多得多。
李教授说,宋江实有其人不假,但史书中反映他的事迹记载却不多,作者举了几部史书,只提到宋江曾经“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被张叔夜“伏兵乘之,江乃降”“诏招抚山东道宋江”。连谁招安的也没说清。至于李教授举的梁中书、梁子美、高俅、蔡京等,只是一些次要人物,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们与宋江及梁山有什么直接关系。《水浒传》中写的梁山泊108名兄弟。有些在史书上还有“一些影子”,但大部分是虚构,是艺术形象。
谈到杨家将,李教授说,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也能在史书里找到一些影子,但仔细一核对,除了杨业和杨延昭之外,很少能见到与史实相吻合之处。这话就有些罔顾事实了。在宋代史料中(包括元明),杨家将的史料很多,几个主要人物不是只能找到“一些影子”,而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早在杨业殉难后,杨业的事迹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欧阳修在给杨业侄孙写的《杨琪墓志》中就说,杨业、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绝不是“谀墓”。杨业殉国后,受到潘美等人的栽脏诬陷。李若拙曾写《杨继业传》为杨业辩诬申冤,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在宋代的几部重要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隆平集》(曾巩)等都有杨家将的记载。元代编写的《宋史》有业、延昭、文广三代的传记。李教授未提杨文广,杨文广曾跟随狄青西征西夏,南平傜乱。杨家将的一些主要部将如焦赞、孟良等,在史书里也能找到“一些影子”。
杨家将的对手辽国的萧太后、韩德让、耶律休哥、肖咄李等也都是历史人物。《杨家将》小说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所依据和运用历史事实比《水浒传》多得多。《水浒传》比《杨家将演义》高,不在于运用和依据的史实多,而是创作水平高。不能因为《水浒传》比《杨家将》艺术水平高,就无视这些史实。
二、关于潘仁美的问题
我觉得李教授的本意是通过这篇文章为潘美鸣不平,认为《杨家将》“胡说八道,虚假编造”,严重扭曲了历史真实,把为大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潘美塑造成了千人不齿、万年遗臭的白脸大奸臣。他把宋太宗雍熙北伐杨业被主将监军迫战殉国的罪责全推到监军王侁身上,把潘美洗涮的干干净净。这是完全不顾史实的说法,许多宋史杨家将研究专家以史实为根据,认定杨业的死,作为主将的潘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只是“领导责任”,有些学者认为潘美是害死杨业的元凶。
关于潘美被塑造成白脸奸臣形象,这是艺术创作问题。杨家将小说、戏剧、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把潘仁美塑造成奸臣形象,虚构了许多他迫害杨家的情节,但潘美只是潘仁美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杨家将中的潘仁美并不等于历史上的潘美,只是迫害忠良的奸臣,是艺术形象。
李教授竭力为潘美辩护,抱不平,认为不应该把潘仁美塑造成奸臣形象。但前面我们已说过,在杨业战殁问题上,潘美应负主要责任,说他是迫害杨业的元凶不为过。
李教授说,“历史的真实究竟为何呢?”历史真像并不像他认定的那样,这里我们不再评叙雍熙北伐全过程了,只就潘美在杨业之死问题上所应负的责任做些分析论断。
从宋朝廷北伐大形势看,曹彬率领东路军和田重进指挥的中路军已经溃败回撤。宋太宗命令西路军掩护云应寰及朔州民众内迁。此时辽十万大军在萧太后亲自督战,耶律斜轸率领下向西路军压过来,先在飞狐口打败宋军,继而收复寰州等地。此时形势危急,不仅关系到能不能完成掩护四州百姓内迁的任务,由于部队行动缓慢,也关系到西路军能不能全身而退的问题。潘美作为主帅,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而且刚从飞狐战败,不可能不清楚西路军所处的形势。面对这种局势,杨业提出建议,“今辽军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时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立于谷口,以骑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杨业提出的撤退方案是周密而切实可行的。但监军王侁、刘文裕却反对杨业的建议,反而迫杨业率军向辽军主力发动进攻。如果说王侁不懂战事,又对杨业有偏见,作为主帅,能征惯战的潘美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弊,但他没有采纳杨业的建议,而是顺从王侁。杨业只得返身率领孤军出击,入陈家谷口时,对潘美指着谷口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杨业率军进入山谷,中了辽军的埋伏,辽军先以佯败引诱,后伏兵四出,宋军惨败。杨业率残余部队且战且退,当抵达谷口时,潘美早已率兵逃跑,杨业只得继续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马被射伤,落马被俘,绝食而死。
请看李教授是怎样为潘美开脱的,他说杨业请求潘美在谷口接应,潘美采纳了杨业的建议,“即陈兵谷口”,后来王侁知道杨业兵败逃跑”,“美不能制”,也跟着跑了。“美不能制”的记载本来就是为潘美开脱,因为带兵的主帅是潘美,不是王侁。而李教授却说,“从中可以看出,杨业的失利乃至殉国,完全是监使王侁起主要作用。事后处理,太宗只给潘美降官三级,是因为潘美只负领导责任,王侁是直接责任人。”为了为潘美开脱,李教授还专门说了监军的厉害。举慕容延钊被监军气的吐血而死。但宋朝的监军制度是代表朝廷监视将帅,不是让监军代主帅指挥军队打仗。事实是潘美带着部队逃跑了,不是王侁带着部队逃跑,宋太宗在褒奖杨业的诏书明确指出“群帅败约,援兵不前”。太宗从轻处罚潘美,不是因他只“负领导责任”,恐怕是因他是“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
三、关于杨门女将和对《杨家将演义》的评价
李教授借给潘美翻案,否定《杨家将演义》,认为是“一本胡说八道虚假编造的小说”。说这本小说不仅严重扭曲历史的真实,把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潘美塑造成千人不齿、万年遗臭的白脸大奸臣。而且扭曲甚至颠倒历史,他举太尉党进捉拿潘美交寇准审判的描写可笑之极,说此时党进已死去9年了,还说历史事实是寇准与杨业不同时,不可能审判潘杨案,并说小说不是不能虚构,但如此虚构法,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历史,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了。但这并不是写可歌可泣的中国历史,是写小说。因塑造人物的需要,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写党进、寇准也不算什么问题。更使李教授看不惯的,是《杨家将演义》塑造了杨门女将的形象。李教授说:“更可笑是杨门女将,个顶个儿都是女强人。不但宋朝的男人都成了废物点心,连辽国大将也怕的要死。十二寡妇去征西,连烧火丫头杨排风都能以一胜百,大宋朝的爷们都死光了,就敢这么掌控‘女士优先’的原则,这样的王朝还怎么维持呀?”就因为塑造了几个女将形象,就是欺宋朝的男儿成了废物点心,就预示大宋朝的爷儿们都死光了。这种说话口气,在《杨家将演义》中也有,不过出自于杨门女将对手辽将夏帅之口。历史事实是宋朝对外作战败多胜少,也不能说宋朝无优秀将领,但宋朝从立国开始就防范猜忌武将,故宋朝的武将多数为悲剧英雄。
李教授还说,“戏说其实是害死人。长期以来,调唆的代州杨家和大明潘家的后裔仇怨日升,势同水火。全然是《杨家将演义》即后来演绎者之过也。”其实潘杨后裔的积怨不能全归咎于杨家将小说,杨家将产生于明代,在此之前,受宋话本金元戏剧的影响,民间已经有了这种情绪,开封还有潘杨湖一边水清,一边水浊的事实,也反映人们对忠烈之后和奸邪之辈的爱憎情绪。
那么《杨家将演义》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小说呢?开始我们就讲了它的艺术性不如《水浒传》,但也不能说它是一本“胡说八道虚假编造”的小说。
《杨家将演义》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北宋以杨业为首的麟州杨氏几代为抗击外族入侵,保家卫国,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杨家虽受到奸臣陷害和被朝廷冤枉,但他们初衷不改,始终怀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感情奋战沙场。男人死了,女人继续战斗,被李教授嘲笑的杨门女将,正是作者打破‘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塑造出的巾帼英雄形象。以佘太君、穆桂英为首的杨门女将更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妇女形象,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包括正反两方面。总的看,《杨家将演义》所讲的故事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为人们所喜闻乐道,后人不断改编,笔者手头就有十余种版本的杨家将小说,杨家将的故事在近现代仍然被不断的改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戏剧中的《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以及大量的优秀影视剧。杨家将文化以各种艺术形象讲述杨家将的故事,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
当然,杨家将小说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它产生于封建时代,存在着一些落后的观念,其中有糟粕,如散布“因果报应,迷信鬼神”等。
这里不是专门评价杨家将小说,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谈些看法。对于杨家将系列小说,历代评论很多。总体说来,小说的观念还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它所宣扬的英雄和爱国是永远值得提倡的。
附:李之亮原文
《水浒传》比《杨家将》更真实
同是写宋朝故事的小说,《杨家将演义》和《水浒传》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按现在的流行说法,《杨家将演义》属于“戏说”之列,是穿着宋朝人的衣裳说明朝的事儿;而《水浒传》则属于“正说”,讲的实实在在就是宋朝的故事,只是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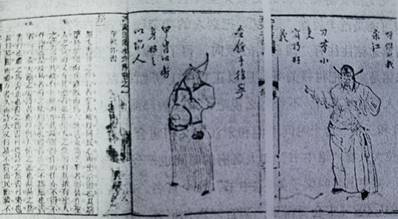
《评论出像水浒传》(清刊本)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141卷明确说:在征讨方腊的战役中,宋江作为马公直(当时围剿帮源洞三军之一)大将王涣的副将,直接参与了端掉“恐怖分子”方腊老窝的战斗,时间在徽宗宣和三年(1121)的四月,也就是《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受招安之后的几个月。宋代史籍中关于宋江的记载还是蛮多的,时间、地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大致脉络则没有太大的出入。如《东都事略·张叔夜传》说张叔夜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知州时,宋江曾经“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张叔夜“伏兵乘之,江乃降”。《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宣和三年五月三日,知海州张叔夜“进职一等”。张叔夜这一次进职,主要功劳就是降伏了“剧贼”宋江。其实宋江闹事儿早在宣和元年(1119)就开始了,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明确记载,宣和元年十二月丙申,“诏招抚山东道宋江”。至于宋江究竟是哪位大将招安的,除了《水浒传》和上面所说的张叔夜之外,还有一个版本称是河东大将折可存(《杨家将演义》所说佘太君家族的后代)所为。宋人范圭《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说,折可存在征讨方腊的战斗中充当第四将,勇擒方腊后回师北上,“班师过国门”的时候,“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擒获”。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一是和宋江先受招安后征方腊的史实完全不符,二是类似的记载仅此一见,很可能是范圭故意“犯规”,把别人的功劳硬扯到折可存身上。古人写墓志铭往往有“谀墓”的倾向,得了钱财丧了良心——请人写墓志铭是要大把付钱的呀,所以正直的士子如苏轼、司马光等人极少给人写这类东西。不管怎么说吧,宋江曾经闹事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宣和三年”这个时间不但和宋江起义相吻合,且与《水浒传》里另一位大人物“梁中书”知大名府的时间也严丝合缝儿。
梁中书名叫梁子美,“中书”是个官名。此人是山东东平望族梁适的后代。《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记载:宣和二年二月九日,大名府知府梁子美“提举西京崇福宫”据《宋史》、《东都事略》的《梁子美传》以及《宋会要辑稿》等书记载,这个人在徽宗即位时担任河北都转运使,召为户部尚书兼知开封府。大观元年(1107)拜尚书右丞,迁左丞(相当于今国务院副总理),加中书侍郎,这是他一生仕宦的巅峰时期。大观二年,因政治倾轧出为郓州(今山东东平)知州,改大名知府。政和三年(1113)再次倒霉,责居单州(今山东单县)。政和六年(1116),再知大名府,四年后致仕,宣和五年(1123)卒,活了七十八岁。梁子美的神道碑如今就在山东东平梁氏家族墓群内,立于宣和七年(1125),碑高7.5米,碑文竖刻43行。民国梁星垣修纂的《江西梁氏家谱》称,梁子美即其家族之始祖,可见这段历史不是施耐庵编造出来的。
为了巴结蔡京,巩固自己的地位,身为大名府知府的梁子美特地献上所谓“生辰纲”,就在情理之中了。《水浒传》作者遣词用语很符合当时的习惯。梁子美给蔡京的礼物为什么叫“生辰纲”,而不叫“生辰礼”呢?第一是因为在宋朝,“纲”就是“纲运”的意思,强调的是成批而不是单件的“运输”之物,譬如书中多次说到的“花石纲”也称为“纲”,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百官在蔡京生日时必须送礼,这在北宋末年已经成了规矩。瞿宗古《归田诗话》里说:“蔡京生日,天下郡国皆有贡献,号‘生辰纲’。”《宋史·宰辅表》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魏国公蔡京“以太师、鲁国公致仕”,说明“太师”这个官称,作者也用得非常准确。称高俅为“太尉”,也合于当时制度。《宋史·徽宗纪》:“(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与《水浒传》所称完全吻合。
在这部小说里,处处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大背景的真实,比如高俅的发迹、徽宗的荒淫、蔡京的书法、汴京城里的彩山、京城名妓李师师等,几乎都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北宋四大书法名家本来应该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京,因为蔡京作恶多端,后人才将他巧妙地换成了蔡襄,都姓蔡嘛。《铁围山丛谈》说:“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意思是到了哲宗绍圣年间,蔡京被公认为天下书法第一人,并非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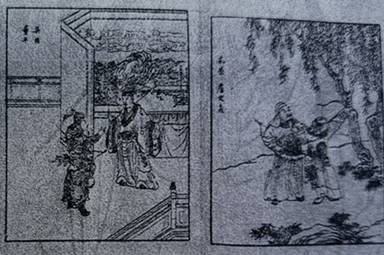 “神行太保”戴宗的出现,也是宋朝特有的现象,因为宋朝传递紧急公文的差人很多都是凭着两条腿递相传送(即每个
“神行太保”戴宗的出现,也是宋朝特有的现象,因为宋朝传递紧急公文的差人很多都是凭着两条腿递相传送(即每个
《水浒全图》(清光绪刊本)
军卒负责一段路程),而不是像唐朝那样一路骑马。这种人当时叫做“急足”或“急脚”,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该书《官政》卷一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又俗称为“急脚子”(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文集里都有所提及)。这又说明施耐庵对当时的军事制度乃至风土民情都十分熟悉,说的全是内行话。
再如鲁智深嘴里经常引以为豪的上司“小种相公”和他哥哥“老种相公”,也都于史有征:小种指的是西北骁将种师中,老种指的是种师道。《宋史·种师道传》说:“时师道春秋高,天下称为‘老种’。”
 在历史大背景真实的前提下,作者再杜撰几个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之类的小人物,使全书鲜活生动,使读者宛如回到了那个遥远而又真切的年代,既没有欺骗世人,又彰显了作者的好恶,正儿八经地演绎历史,难怪被后人公认为名著,自有它的道理。
在历史大背景真实的前提下,作者再杜撰几个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之类的小人物,使全书鲜活生动,使读者宛如回到了那个遥远而又真切的年代,既没有欺骗世人,又彰显了作者的好恶,正儿八经地演绎历史,难怪被后人公认为名著,自有它的道理。
《杨家将演义》就不一样了,小说里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也能在史书里找到一些影子,但仔细一核对,除了杨业和杨延昭之外,很少能见到与史实相吻合之处。
潘美像
描写最糟糕的当属潘仁美。历史上真实的潘仁美名叫潘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铁哥们儿,曾参与过陈桥兵变,而且是“核心组”成员之一。赵匡胤从陈桥驿开回汴京城之前,特派潘美打前站,赶到朝廷向后周大臣们宣布周朝结束、新皇帝即位。此后的太祖朝中,他又参加了平定淮南军阀李重进叛乱(担任副帅)、守卫新复领土湖南而狙击来犯之敌(任主帅)、收复两广南汉刘氏(任主帅)、李煜的江南大国南唐(任副帅)、收复刘继元的河东北汉(任副帅,可惜未能收复)等重大战役。太宗即位后,又以统帅的身份一举拿下太原,收复北汉,紧接着挥师北上,攻取燕云十六州,可惜再次功败垂成。
雍熙四年(987),太宗经过周密的部署,派曹彬为东路元帅,田重进为中路元帅,潘美为西路元帅,向契丹发动了全面进攻。也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由于种种原因,潘美没有采纳西路副将杨业的建议,致使大军失利,杨业父子战死在陈家谷口。为了惩戒败军之将,太宗将潘美连降三级,勒令他“居家待罪”,一年之后,才命他担任真定(今河北正定)知府,改任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宋史·太宗纪》记载,淳化二年(991)“六月甲戌,同平章事潘美卒”于太原。
这位为大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在《杨家将演义》里,却成了个千人不齿、万年遗臭的白脸儿大奸臣,这本身就严重歪曲了历史的真实。
其实这本书歪曲甚至颠倒历史,还不仅仅表现在潘仁美一个人身上。在《寇准勘问潘仁美》这一回里,写杨六郎从前线回到汴京告御状,太宗勃然大怒,立马儿派“太尉党进”到雁门关去捉拿潘仁美。党进顺顺利利地把潘仁美押到了太原府,交给太原府尹寇准严加审判。这一段描写真是可笑之极。历史上真实的党进是位目不识丁的武将,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在担任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帅时误食毒蛇,没几天就死了。太平兴国三年距杨业殉国的雍熙四年还差九年,按《杨家将演义》的说法儿,党进是死了九年以后又从棺材里爬出来,赶到雁门关去捉拿潘仁美的。
历史上真实的寇准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此人也算个神童,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当了几任地方小官,回到汴京,又干了几任经济方面的官。此人有点儿愣头儿青,有一回在太宗面前奏事,太宗不爱听了,抬起屁股要走,寇准一把拽住太宗的龙袍让他坐下把话听完。太宗感到此人不同寻常,大为赞赏地说道:朕得寇准,如同当年唐太宗得到魏徵!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淳化元年(990)。而杨业死于987年,也就是说,杨业死的时候,太宗还根本不认得寇准呢。书里还说寇准是从“左丞相”贬到太原来的。查查史书,不对呀,寇准第一次当宰相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这一年杨业已经死了十八年;第二次是在真宗天禧三年(1019),这一年杨业已经死了三十三年。其实杨业殉国的时候,寇准刚刚中进士而已。再说寇准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太原府尹。
小说不是不能虚构,但如此虚构法,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历史岂不成了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了?
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人对本书的荒唐写法深感气愤了。譬如清朝人昭梿在他的《啸亭杂录》中就说:“委巷琐谈虽不足与辨,然使村夫野父闻之,足使颠倒黑白。如‘关公释曹’、‘潘美陷杨业’,此显然者。”人家潘美是元帅级的英雄人物,又是在大敌当前的当口儿担任一路总指挥,从哪个角度也没有必要非把自家的副将杨业害死呀。遗憾的是,昭梿深感气愤的现象在文化畸形繁荣的今天愈演愈烈,比《杨家将演义》更邪乎的戏说大量涌现。这种不怕被后人笑骂的勇气实在令人感到惊愕——《杨家将演义》好赖还有一条颂扬忠勇贬斥邪佞的红线,今天一些所谓吸引眼球的“作品”,恐怕只剩下捞银子一个目的了。
历史的真实究竟如何呢?且看《宋史·杨业传》的那段记载:雍熙三年,大兵北征,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蔚州刺史王侁为监军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当时契丹国母萧太后亲帅大军十余万,夺回被宋朝收复的寰州。杨业对潘美等人说:“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并拿出了自己的一套行动方案。监军使王侁反唇相讥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意思是你杨业素来被称为“杨无敌”,如今大敌当前,你反倒乱扯因由不想作战,是不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杨业有口难辩,仰天长叹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临行前,指着陈家谷口说道:“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潘美采纳了杨业的建议,“即与王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作为史书,记载不算不详细了。从中可以看出,杨业的失利乃至殉国,完全是监军使王侁在起主要作用。难怪杨业死后,太宗的处理意见是“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潘美负领导责任,降官三等;王侁直接导致战事失利,是直接责任人,除名为民、金州编管。可以证明,杨业所谓的“奸臣”指的是王侁而不是潘美。
也许有人会问:你潘美不是总指挥吗?凭什么要听从监军王侁的一面之词?难道总指挥还惧怕监军不成?还真说对了,自打唐末五代以来,朝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军队,一定要在统帅的头上安把刀——派亲信“监其军”,防止统帅胡来或者哗变。这是啥意思,很容易理解。五代末宋初偏国后蜀、南汉、南唐的失利甚至亡国,让赵匡胤屡屡得手,都和他们的监军使与统帅搞摩擦有直接关系,看看《资治通鉴》就全明白了。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这方面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严。建国初年收复湖北和湖南时,年轻气盛的监军使李处耘硬是把总司令慕容延钊气得吐血而死,厉害不厉害?
由于《杨家将演义》以极端的笔法描写忠奸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所以后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添枝加叶,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什么四郎探母啦,三关排宴啦,都出来了。更可笑的是杨门女将,个顶个儿都是女强人,不但宋朝的男人都成了废物点心,连辽国大将也怕得要死。十二寡妇得去征西,连烧火丫头杨排风都能以一胜百,大宋朝的爷们儿都死光了?就敢这么掌握“女士优先”原则?这样的王朝还怎么维持呀?
“戏说”真是害死人,长期以来,调唆得代州杨家和大名潘家的后裔仇怨日深,势同水火,全然是《杨家将演义》及后来演绎者之过也。历史上的杨家和潘家本来都是赵宋王朝的大功臣,其子子孙孙都有资格因宋朝那段历史而引以为豪,却被一本胡说八道虚假编造的小说搞得反目成仇,实在是天大的悲哀。
(转自《教科书里没有的宋史》)
(作者 李之亮,河北省黄骅市人,宋代文学、文献、文化史学者,古文献学教授。已出版著作五十余部。《张舜民诗集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王荆公诗注补笺》、《王荆公文集笺注》为作者研究宋代文学的代表作;《宋代郡守通考》、《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京朝官通考》、《宋史全文》为作者研究宋代史学的代表作;《海录碎事》为作者研究宋代文献的代表作;《周邦彦姜夔张炎词选》、《白话宋词三百首》、《唐宋文库》为作者宋代文学普及读物的代表作。其中《宋代郡守通考》(十册)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目前承担的还有《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司马光集编年笺注》等国家科研项目。《赵宋王朝》是其第一部大型长篇历史小说。)